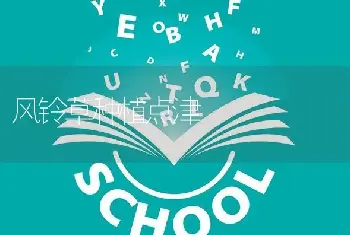杜鹃花(学名: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又名映山红、山石榴,为常绿或平常绿灌木。相传,古有杜鹃鸟,日夜哀鸣而咯血,染红遍山的花朵,因而得名。杜鹃花一般春天开花,每簇花2~6朵,花冠漏斗形,有红、淡红、杏红、雪青、白色等,花色繁茂艳丽。生于海拔500~1200(~2500)米的山地疏灌丛或松林下,为中国中南及西南典型的酸性土指示植物。

由于产量不高,无法带来梦想的经济收益,许多野生资源渐渐被淡忘、埋没甚至铲除。陈瑞阳曾在资料中得知,海南某地有野生稻,寻去后只看到一片楼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籍华人徐道觉按照对自己从世界各地收集回的各种哺乳动物组织样本和淋巴细胞进行染色体解析的结果,主编了《哺乳动物染色体图谱》,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1977年出版第十卷,历经10年。
动物染色体图谱问世后的第二年,中国也走到了一个关键期间。“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想做个别工作。”年逾不惑的陈瑞阳决意从事基础性研究,靠着自创的独特操作对策,他开始四处采集各栽培物,进行染色体研究。
30年后,由南开大学陈瑞阳教授编著、在研究领域内填补了国际空白的《中国重要经济植物基因组染色体图谱》问世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基因组染色体图谱。
陈瑞阳说,中国是世界上种植作物最早和最大的起源地,至今在全国各地还成长着许多珍贵的种植作物野生祖先及其近缘植物,如野生大豆、野生稻、野生茶和各种野生果树等,“英国皇家植物园里的杜鹃,均是来自中国。”
它叫“基因组染色体图谱”
最近,学校里认识的人见到陈瑞阳,都会向他提起此书,不过表达不一。其实,有两个说法是陈瑞阳不太附和的。
他数次强调,这是“基因组染色体图谱”,和基因图谱不一样。时下热点的“基因图谱”是指经过测序得到的DNA上各碱基布列的次序,最终得到的是一部写满四种碱基(A、T、C、G)的“基因词典”。在这本词典里,我们能够查到,何种基因抑制生物的何种性状(例如肥胖)。“基因组染色体图谱”则是经过处理分裂中期的细胞,并用相机拍摄得到的染色体形象。
在基因测序大行其道的今天,几乎全部的实验、全部的文章都以挂上“基因”“序列”之类的名号为荣。但是,我们不应该淡忘曾经为遗传学作出贡献的染色体。作为携带千万遗传物质的载体,染色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一向是生命科学中的主要基础研究领域。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结构具有种的特异性,是遗传学、细胞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分类学的主要基础。
尽管“基因图谱”和“基因组染色体图谱”有着共同的目的——了解编码生命遗传的信息,但如果将前者比作城市中每个院落的具体信息,后者则更像一座城市的地形图,其它,陈瑞阳也区别意“基因组染色体图谱绘制成功”的说法。
“是相机拍摄,并非绘制。”过去,大多数利用相机经过显微镜的目镜为染色体拍摄写真,将胶片冲洗放大成照片后,再将照片上每条染色体分别剪下,配对布列,粘贴成一张“排排坐”的照片。
《图谱》共5册,包括中国果树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中国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中国园林花卉植物、中国竹类、中国药用植物的染色体图谱,为种植植物的杂交育种和起源进化供给了基础资料——其中,第五册采用了数码拍摄技术。
从2007年开始,陈瑞阳开始将显微镜与数码相机相连,染色的图像能够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经过图像处理软件能够得到更为清晰详尽的染色体照片。
为什么面世更晚的是植物图谱
其实,实验过程中有比“手工绘制”更精巧也更困难的手工技术:对植物细胞壁的解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项手艺活,需要能工巧匠。
和动物细胞相比,植物细胞要多一项构造:最外层的细胞壁。在制作染色体材料的过程中,比较梦想的情况是得到单个分散的细胞,这样才能看清每个细胞中染色体的集体全貌。但是,由于区别细胞的细胞壁相互连接,在制作染色体时,植物细胞很容易混做一团。因此,要得到好的染色体照片,务必先将细胞从细胞壁中释放出来,前提是先将细胞壁解离。
其实,要解离细胞壁,原理也简单,利用纤维素酶或果胶酶溶解。只是,这看似简单的原理,执行起来着实不易。如果酶过少或者解离时间过短,则不能有用分散细胞;反之,细胞壁分解过度可能引起染色体游离到显微镜视野之外,而无法找到合适的观察对象。再者,处理的时间,压片时的轻重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除扎实的生物学理论外,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又多添一项:手艺精湛。
野生物种在消逝
不过,酿成植物染色体图谱远远晚于动物的起因不止这些。
若沿着时间链梳理,首先难在跋涉寻找。
上世纪80年代初,陈瑞阳去了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采集野生茶,为了考察野生与种植茶的染色体,判断两者有无亲缘关系,带路的是原本素不相识的云南植物所及农业大学的老师。另一次,是去云南省的一处边远山区,为了寻找柑橘的祖先或野生近缘种红河大翼橙,从昆明出发,开车一周才到达目的地。陈瑞阳说,在图册的末尾感谢了109位个人及50家机构,但也只是不完全统计。“例如去海南岛采集野生稻,由当地人带领,走了一天的路,我却连人家的名字都忘记了。”
比起跋涉的劳顿,更令人沮丧的是物种的消逝。
陈瑞阳不无苦涩地讲了一则笑话:一对美国夫妇来中国采集野生大豆,四处寻觅未果,坐在公园休息,丈夫一回头,身后就是一株野生大豆。由于产量不高,无法带来梦想的经济收益,许多野生资源渐渐被淡忘、埋没甚至铲除。陈瑞阳曾在资料中得知,海南某地有野生稻,寻去后只看到一片楼房。
再次是取材。因为要看到染色体,必需采集活的处于分裂活跃期的植物材料(通常是萌动的根尖和芽)。但是,并不能肯定采集的样本是否正处于分裂期,“植物也可能在睡觉呢”。事实上,植物细胞大多数数时间都在“睡觉”,但不是完全休息——处在分裂间期的它们,忙于完成DNA和蛋白质的复制。可是,能观察到成形染色体分裂期的,因物种而异,只占4% ~10%。以蚕豆19.5小时的周期为例,分裂期只有2小时,其余17个半小时,无法观察到成形的染色体。
图谱第四册的主角是竹子。前两次,陈瑞阳的学生去了江西等省份,都没有成功,第三次,他亲自去了广东,总算取到了合适的材料。
其它,植物的基因组中染色体数目较多。有些低等植物如蕨类,一个基因组中染色体的数目甚至高达几百条。庞大的数量,也加强了染色体图谱工作的难度。
基础性学科需要更多投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院士洪德元介绍说,我国目前有植物5万多种,而拥有染色体信息记录的,还不足20%—— 即使是这一小一些,也只是分散在各类文献当中。
“目前,国内过量注重创新或与生产相结合,对于原创性、基础性的学科研究反而普遍不太看重。染色体图谱的技术纵然古老,但我们需要有人完成这样系统性的工作。”
洪德元和陈瑞阳都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基础性学科研究申请经费困难,而且不易取得突破性的发现,日久天长待在实验室中,从事资料收集积累的工作,愿意为此投入的年轻人并不多。
但陈瑞阳还是很庆幸,眼下自己实验室里,还有不少踏实的年轻人。“关于物种的起源进化,能够从区别层面去考察,我们的着手点是染色体。许多植物间的亲缘关系从染色体都能看出来。”
洪德元认为,图谱的问世,对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以及农业、林业等产业的扩大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眼下,汇总染色体图谱的工作纵然暂时告一段落,但陈瑞阳构思的工作远未结束。除了近5年来一向从事的改良作物的研究,他很指望能联合计算机专业的研究人员,总结出规律,为这些染色体图谱建立数学模型。“我现在就是年纪大了,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很指望奋力申请建立染色体数据库。”但这可能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