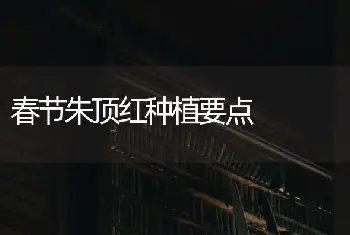在全部的花朵中,恐怕要数兰花——我这里指的是“中国兰”或叫“地生兰”——最“中国”了。历朝历代的中国士大夫们最喜欢三栽培物:松、竹、梅,称它们为“岁寒三友”。松的四季常青、竹的正直有节、梅的傲霜斗雪,使这三栽培物具有一种人格象征。但自《群芳清玩》问世后,作者认为“世称三友,竹有节而无花,梅有花而无叶,松有叶而无香,唯兰独并有之”,兰花便逐渐成了文人学者士大夫案头的最佳清供。或暗示自己所保持的操守,或只为了显示主人的一种雅兴。

以东方的审美情趣看,兰花确实是最具中国味道的。它不是西方人欣赏的那种大红大紫热烈旷达之美,而是像中国人那样婉约、含蓄、清雅,它的枝叶类似一簇翡翠的喷泉,永远透出一种生命的绿意。不刺目,不张扬,青草似的温柔,却又松柏似的坚毅。真个是“不求发泄,不畏凋残”,光是那一丛丛永久的青碧,便足以赏心好看。待到花开时,只消一朵,便满室飘香,靠近闻,又没有了。奇怪的是,便是在它一朵朵盛开之际,也不招蜂引蝶。我种兰花多年,还从未见到过蜂蝶萦绕兰花枝头的。它却又始终悄悄地放出它清醇、淡雅而悠远的芳香。兰花于是赢得了“王者之香”的美誉。又因这香气似有若无,故昔人有句云:“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话不仅赋予兰花一丝神秘色彩,还有点哲学意味:如果我们有机解散一位贤者交往,相处久了,反而觉得他和平常人无异,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兰花的形状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那三片形同花瓣的,其实是花萼,认真看里面还有三小片,那才是真正的花瓣。下面一片形如人的嘴唇,叫“唇瓣”。即便是纯白的兰花,“唇瓣”上也有许多区别颜色的斑点。这斑点颇有考究。那些会“玩”兰花的,认为“唇瓣”那变化万千的色斑才是最具审美价值的个别。从植物学角度看,唇瓣应是长在兰花最上面的花瓣,但由于花梗、子房极复杂的旋转,使花扭转了180度因而唇瓣成了兰花最下面的一片花瓣。兰花的这一奇妙的自然征象,不论从植物学或美学角度来品评,都堪称奇花异卉。最为奇特的还是它的花蕊,不像别的花朵雌雄分蕊,而是在唇瓣上方生成一个合二而一的为兰花所特有的“合蕊柱”。兰花因此被植物学家看做是进化到最高阶段的有花植物。
兰科植物在单子叶植物纲中又是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植物,它仅次于双子叶植物的菊科而名列第二。环球700属20000种,中国占173属1200种。
于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偶合:
哺乳动物中高度进化的人类,爱上了植物中高度进化的兰类;而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尤爱分布广种类多的中国兰。动植物之间的相爱似乎也讲个“门当户对”?
中国人之爱兰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关于“兰”、“蕙”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畹”,古面积单位,1畹相当于现在的12亩,9“畹”就是100多亩了。屈原不是专业户,也无机械化,他种得了那么多吗?另考,古代“兰”和“蕙”据罗愿《尔雅翼》所描写的,是一种春季开黄花,秋季开紫花,花叶有香味的菊科植物。植物学家也认为,这和今天的兰花不是一回事。
那么真正的涉及地生兰的文字始于何时呢?专家们普遍认为是唐代(见唐彦谦的《咏兰》和杨夔的《植兰说》)。前者以诗的文字描绘碧绿弯曲的兰花条形叶在微风中摇曳,苍白的花朵上还凝着露珠:“春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植兰说》则索性是讲地生兰的种植办法了。连唐太宗也写了咏兰的诗:“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兰花因皇帝欣赏士大夫们也就争相栽培,并从兰花的迎风傲雪、隐匿深山、不媚不俗、常青常绿的习性中找到一种隐喻、一种参照,以兰为题材的诗和画开始产生。个别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如李白、苏东坡、苏辙、杨万里都有诗吟咏兰花。如李白“若无清风吹,清气为谁发”、苏东坡“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等等均是名句。最初画兰应数宋十世皇室成员赵孟坚(1199—1264)。宋亡于元,他隐居画兰,以示清高。兰花还因此赋予忠贞的品格。他的堂弟赵孟?名气比他大,因屈于元,有弃宋之嫌,故一生不画兰花。元朝还有个很有名的画家郑思肖(1239—1316)画兰不画土,以抗议元夺宋土,“邑宰闻其精于画兰,不妄与人,贻以赋役取之。怒曰:头可得,兰不可得。”郑思肖此类傲骨反倒震慑了对方,“宰奇而释之”。这类作品与作者人格的一致确乎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幅无土春兰画卷至今收藏在美国华盛顿Freer画廊,确确实实地根无所系了。
关于兰花的欣赏和种植专著也逐渐多起来,从高濂的《兰谱》(1519年)到夏眙彬的《种兰法》(1930年)前前后后林林总总没有完整的统计。中国士大夫们历来以贫寒孤傲为荣,兰花很能满意这样一种心理。所谓“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
此类喜欢兰、写兰、画兰、赏兰的“兰文化”一向延续下来,至清朝的郑板桥能够说到了极至。这位从画像上看骨瘦如柴,风骨和气节也颇似兰花的郑板桥,在题一幅兰花时写道:“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香稠,非无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最深刻地面达了作者借兰花自诩,鄙薄脚下过眼烟云般的功名利禄的气节,一派清高孤傲的寓意跃然纸上。由于郑板桥对兰花的挚爱和过细的观察,使他所画的一幅幅兰花飒飒若有生命,馨然似送清香。这些字画已经成了世界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珍宝!纵观历史,全部的花朵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种花朵像兰花那样与中国文化结合得那么紧。
因之,世界植物学界把兰花中的地生兰一属郑重地命名为“中国兰”(OrchisChina)。
中国兰自然以中国为多,而在中国又以云南这个地球村的花园里最多,它仍是集中在这个花园最美丽的地方——滇西北的崇山峻岭中。《徐霞客游记》称云南宾川的“鸡足山兰品最多有。所谓雪兰(斑白)、玉兰(花绿)最上,虎头兰最大……”《云南通志》载:“兰有七十余种,雪兰为胜。”在这个地球村的花园里,一丛丛中国兰,或摇曳于悬岩峭壁,或怒放于激流山溪、高山深谷、雪岭冰漠,处处都有它们的芳踪。
即便是在我国分布范围很窄的另一属兰花——“附生兰”(“热带兰”、“洋兰”),在我们地球村的花园南端的热带雨林中也能找到。它们寄生在雨林的巨大乔木上,当七彩斑斓的花朵争相怒放时,时而交织、架构成一座座“空中花园”,蔚为大观。
兰属的花朵由于其倒转的唇瓣酷似一叶小舟,因之又有一个拉丁文名Gymbidium(小舟),此类变种在洋兰中尤为显著。如杓兰、兜兰等等。有时,整个花朵就是个圆筒,形象很怪诞。西方人后来索性就把兜兰那变大了的“小舟”改称为“夫人的拖鞋”。从这些名字能够感知这另一属兰花的“洋”味。为了有别于中国兰,又叫它“洋兰”。“洋兰”就是以它花形怪诞、色彩艳丽吸引人,一般有色无香。
中国人之喜种中国兰,原来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在今天还暗示一种清高,那也只是拒绝媚俗的一种精神向往和淡泊富贵的廉洁矜持。想想高度商品化的社会,这委实也可笑。对某些人而言,今天的兰花已不是郑板桥的兰花了。它已代表着金钱,甚至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现在“玩”名兰者,早已不是穷酸的郑板桥,而多是些大富大贵之人,这也是这位板桥道人始料不及的。
由于市场看好,利润丰厚,极大地带动了地生兰的种植和扩展(洋兰也不例外),个别新品系不时培育出来。滇西的大理、丽江、保山,滇南的建水、石屏,滇东的文山、西畴,以及省会昆明,是历史上滇兰的种植中心。除大小雪素、春兰、墨兰、剑兰、朱砂兰、双飞燕等等传统品系之外,新培育的滇兰品系还色香兼具,有了什么“绿素”、“红春素”、“金黄素”等等新品类。“金碧交辉”、“黑珍珠”、“龙眼珠光兰”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1990年,维西县一个农民培育出一盆“太白素”,共4苗,送广州兰花博览会参展,外商开价4万美元仍未成交。闻之无不咋舌。
今天的中国兰,就其外观形象和人格象征,随着商品化而大大地异化了。现在种兰花,买兰花,少有什么精神寓意,更多的是功利和实用:用于市场谋利,用于室内装点,用于送礼应酬。送人参燕窝,送人头马,送劳力士都贵,但都刺眼,都俗气,送一盆高档兰花就绝无行贿之嫌,而且是何等的高雅!贵重程度只有收、送双方知道。一般人还不是把它当成一盆普通花卉,自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摆在客厅里供人欣赏。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达官贵人家里名兰多多。
物以稀为贵。地生兰中,且不论大小雪素墨兰这些传统名品,更不敢谈“太白素”那样近十万人民币一苗的珍希兰花,便是“下山草”——刚刚从山上采来的兰花,其价格亦不菲。为了图利,什么都假,兰花又焉能例外。多年前,我就因买兰花上了一次当。花鸟市场那小贩直说他的兰花是真正的“素心兰”,指给我看那花朵,说还会抽出好几箭的。我是历来什么都信以为真,看那卖花人憨厚巴交一副山里人的样子,便毫不犹豫地掏出50元钱买了。回到家,还挺兴奋地请一位懂兰花的朋友来看,他喜笑颜开,说这是“麦冬”,并毫不犹豫地把花拔起,在花茎和根之间,一根极细的牙签露了出来。我一下子感应非常沮丧。这是一次真正的“移花接木”,而且成功了。作假者认为你是傻瓜,而你确实也是。
“麦冬”一名“麦门冬”,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条形,丛生,酷似兰草。它本是一味不错的中药,一冒充兰花,便假了。
上了一次当并未影响我种兰花的兴致,到现在我还养了几盆。我的种兰,自是不为显示清高,仅仅是.因为懒。懒得侍候那些金枝玉叶。兰花一点不娇嫩,一盆山土,一杯清水便活了。只要每周浇一次水,放在背阴处,春季那一箭箭花苞就在你疏忽它的时候,突地从一丛青碧中蹿了出来,给人带来阵阵惊喜。悄悄开放的兰花还会让我想起边疆那不受污染的深山幽谷和生活在其中的不受污染的心灵。我想起1978年我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看到的一丛野生兰花,也是悄无声息地开放着,芳香着,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它的花朵,嗅到它的芬芳。“不以无人而不芳”,这很像生活中的某些人。我从没写过小说,却因这次感受写下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空谷兰》,它给我带来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我的爱兰也许是从这时开始的。
更早一点,我的爱兰恐怕要从“吃兰”开始。那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随叔叔们上山砍柴,肚子饿极,叔叔带我走进一个守包谷地的窝棚里,守地的老人一边在火灰里烧包谷,一边煮着一锅什么。叔叔问是什么,老人说是山里面挖来的天麻,挺补人的。边说边刨出烤黄的鲜包谷,捞出一块天麻,两种东西都那么鲜美脆嫩。也许是饿的,我一口烤包谷,一口白水煮天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了。最近查资料,才知道大名鼎鼎的补药天麻,植物学上也是兰科植物的一种。我的爱兰不是从“吃兰”始么?
天麻作为兰科植物是开花的。可惜我没见过天麻花。它长年成长地下,开花时才钻出地面,抽出花序。经植物学家多年观察、研究,才知天麻是依靠密环菌供给养料、水分而成长的。现已解决它们的养殖问题,天麻能够大面积人工种植了。兰科植物的这一贡献,爱兰者未必知道。
随着兰花的进入市场,兰花(特别是名贵兰花)已经是金钱的代名词了。但对少数人,兰花还是那株具有人格取向的兰花。“兰花本是山中草”,起码是大自然的一种安慰吧。那些来自东京、汉城、香港的客商们,为什么要到万里之外的云南来寻它的芳踪呢?工业社会,科技文明无疑带给富贵人家巨大的乐趣和安逸,但同时也副产了个别媚俗、艳俗、贱俗的东西。而中国文化赋予中国兰的那种东方神韵始终吸引着人们。正如日本出名兰花搜集家神谷高树说:“滇兰似云岭的蓝天白云,意境悠远,清丽脱俗……”这长自地球村的花园——云南的兰花,无疑会给那些焦灼的心灵以都市生活无法得到的滋养和慰藉。
郑板桥还有个名句云:“难得胡涂。”甚妙。妙在旨意是双向的:一方面说一个人胡涂很不易,所以才“难得胡涂”;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学会胡涂也就“胡涂难得”了。
我想,此翁若是活到今天再画兰花,很可能还再题一句:
“难得清高”——清高难得。
兰花因此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