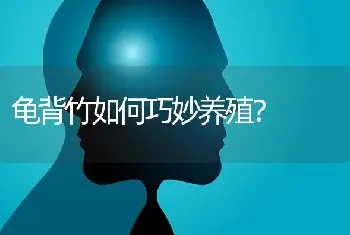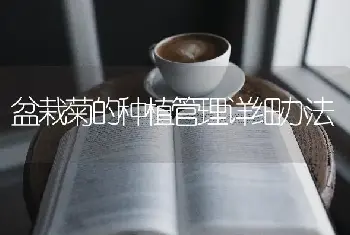或者,我是受文森特·凡高的画影响太深了,我至今相信向日葵不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它更像是上帝的信使。秋季的田野,向日葵成片地开放,将太阳无数倍地放大,将日光聚集在一起,也将秋季的金黄色调无与伦比地渲染和夸张。这是一种让人忧郁或狂躁的颜色,它的颜色黄铜一样融化,将全部的锋利化为虚无。或者,将虚无的日光无数倍地浓缩,直至成为一种真实的物质。我不敢直接触摸它的金黄,它应该还有着炽热的温度,它有着日光般纯粹的结晶,而不是黄铜的冰冷身体。我的目光被它狂潮般的金黄色所淹没,我感觉到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战栗,这是一种我应该畏敬的生命。它执著地将脸始终朝向太阳,秋季的天空纯净得无以比拟,那种蓝色是一种冷静的、低沉而博大的心情状态,太阳孤独地漂泊于天空,它的光线多么忧郁而孤独。秋风拂起大地的尘埃,向日葵姿势优雅地微微倾斜,一种来自于灵魂或者天堂高处的歌声自心底响起。这是一种绝唱,秋草凋零的田野,生命的迹象日渐消逝,向日葵独自承担起生命歌者的角色。宽大的叶片已经不再像夏季那么滋养和浓艳,一种经历沧桑的疲惫和颓然写满了每一片叶片。

我看到在秋季的原野里收拾着最后几片玉米地的农者,他们无不俯伏着,向着大地深深地弯下腰。已经死亡的玉米棵一行行站立,叶片枯萎了,饱满的穗依然像另一个待发的生命一样光彩炫然,我想到了那一只产羔的山羊。玉米地旁边就是向日葵地,这是截然区别的两种世界。相信向日葵是有灵魂的植物,它对于太阳有着执著的崇拜,甚至它可以沉思自然与生命的诸多机要。当凡高画下那些向日葵的时候,一定会被自己的画所震撼,他不假沉思地应用了最适当的颜色和色调,用一种近乎疯狂的颤抖的技巧将内心的感受一点点地涂抹于画布上。那些金黄色至今依然感动着我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永恒的日光留在了他昏暗的画室里,当他的脑海一片迷茫的时候,画上的向日葵让他稍稍冷静了片刻。此类来自于北美荒原的植物,多么狂热地追求着日光。那种金色多么宁静,纯粹得几乎一尘不染。当我走过一片向日葵地的时候,我的身体与灵魂化为一片金黄,它将我融化,直至合而为一。它那暗褐色的花盘,暴突而起的子房,密集而有序的布列,秩序井然的整体,士兵一般。厚实而宽大的叶子,颓然下垂,这是一种智慧和理性的选择。田野上刮起的风将全部的热情和幻想都刮跑了,剩下的就是理性和无奈了。老玉米选择了退出,向日葵在做最后的绝唱。博尔赫斯在诗中唱道: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只剩下了日光。凡高在阿尔的原野里看到的或许就是秋季的向日葵,它显得多么狂野不羁,肆意张扬的花萼——枯干、坚硬、锐利的芒刺,被风吹得失水的花瓣,多么倔强地紧锁着,它有些卷曲,因而显得不太规整有序。那些张扬的楞边和花萼的锋芒刺中了凡高的神经,它那青铜色的光线再一次将他内心的柔弱击碎,他亲吻着失水的花瓣和萼片,他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
那些细微的晶芒,来自于秋季田野的植物之上,泥土之上。绿色正在一点点地被风刮走。日光倾斜着投向大地,向日葵最后占据着的地方,我的精神在一点点接近沸点。
一只山羊的秋季
那是只漂亮的母山羊,黑白相间的毛皮,曲线秀美的轮廓,稍稍磨蚀的犄角,下垂的大耳朵,它的后腿间吊着一只布袋般大小的乳房,随着它的行走而一甩一甩地晃荡。它的主人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五十多岁的老汉,黑瘦、精干,他的一只眼睛缺失,因此,他有时不得不歪着脑袋瞅人或物。从他家到后山约有半里多路程,他天天赶着母山羊上山,走过那些被毛竹林遮掩的小径。那只山羊无论怎样是一只关女山羊,它大而敞亮的眼睛,水汪汪的,它的叫声柔柔而带着迷人的颤音,像花样女高音。它的蹄细小而精致,腿脚修长,腹下的毛细密而稍稍卷曲,像女人披在肩上的大波浪,它足以让另一只陌生的山羊一见钟情。
山冈上除了飘飞着芦花的茅草外,就是齐膝深的藤刺和荆棘,山羊显然不需要那些藤刺和荆棘。他一边用柴刀劈着那些藤刺和荆棘,开出一条适合羊走动和吃食的地方。他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某一个丘垄,那是一块荒芜的园地,他在思忖着那些往事。一只黑白相间的山羊和一个细瘦的老汉成为山冈上唯一的风景。远方是山,再远方,还是山。一只鸟都飞不过那些望不到头的山。何况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汉,他可以看到什么?他可以看多远?他相信,他的婆娘会发生的,她离开家已经整整十年了。他不能肯定她离开时走的是哪条路,往哪个偏向?但他猜测她应该走过这条通往山外的道路,他甚至连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仔细地辨认了一番,一天天过去,他和他的山羊守望着远方的山冈。而这只山羊已通过了好几代,到了如今这只他叫“花花”的母山羊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的山羊了,他的孩子也去了远方,到南方打工挣钱去了,一去也再也没有回来。“花花”又生下了两只羔羊,这是他这个秋季里最大的惊喜。他认为“花花”才是他的子女们,那两只羔羊才是他的孙孙。他亲昵地叫着“花花”,揪下一根柔软的芦苇做鞭子,他从来没有打过山羊的主意——打算吃掉或者卖掉其中的一只或者所有。他认为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情,谁会吃掉或者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女!山羊不知道这些事情,它只知道这里有最肥最嫩的青草,这里可以被山风吹拂,可以望到另一座山的山坡上野草繁茂,可以让它的两只羔痛快地玩耍和嬉戏。
日光密集地照射在山冈上,芦花如燃烧般绚烂,也照射到老汉身上的白袄褂和山羊们。寂静的山冈上,羊欢快地叫着,老汉痴痴地张望,不断大声地吼几嗓门:天上白花花的那个云彩呀,寻不着个门,地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寻不着个人……“花花”抬头看了看主人,它怎么猜得透主人的心事呢。日光落在老汉的脸上,古铜色的脸庞上老泪纵横。沿着一条条细细的沟渠流淌。晶亮的液体坠落,将草砸得直摇晃,似乎很坚硬的泪珠,它会将一块石头敲开缝。他抹了一把脸,叹了叹,狠狠地将手里的苇子杆撅断,又扯下另一根苇子来。沿着那条山道,可以走到下沙和广洋,再往东往南,他就不知晓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走过那条山道,他牵回了一只漂亮的白山羊,同时牵回了他的媳妇。在那条道上,他打死过一条企图咬他羊的野豺,在那条道上,他走失了他的媳妇和孩子们,他狂怒地和个别无辜的树作对,用身上的柴刀胡乱劈斫,结果,他的一只眼睛被碎木屑击中。山荆藤上的刺将他扎得鲜血淋漓,他的山羊惊惶失措,往着荒草深处狂奔而去,再也没有找回来。他捂着受伤的左眼,手里只剩下半截羊绳子,踉跄着走回家。第二天,他在对面的山垄上找到了那只羊的遗骸,不知是什么野物吃了羊,那羊的眼睛依然惊骇地睁着,只是蒙上了一层阴翳,灰暗无光。
山上的房子终于空荡荡了,他和他的羊失去了踪影。在这个秋季,没有任何的消息,走在那条道上,依然是没膝的荒草,已经枯索的草再也直不起身了,它们低伏向尘埃。人和羊的脚印一天天地被风抹平着,终有一天。它会消逝的,和他以及他的羊一样。细碎而混乱的芦花漫天飞舞,秋季已经接近尾声。风加倍凌厉,微微带着凛人的寒意。
一株芦苇折断了,发出一声脆响,又有个别芦苇折断了,折断的还有一个季节,个别故事折断了,它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结局了,可是,明年的春季,芦苇还会纷纷长出来,重新将山冈簇拥和旌扬着。